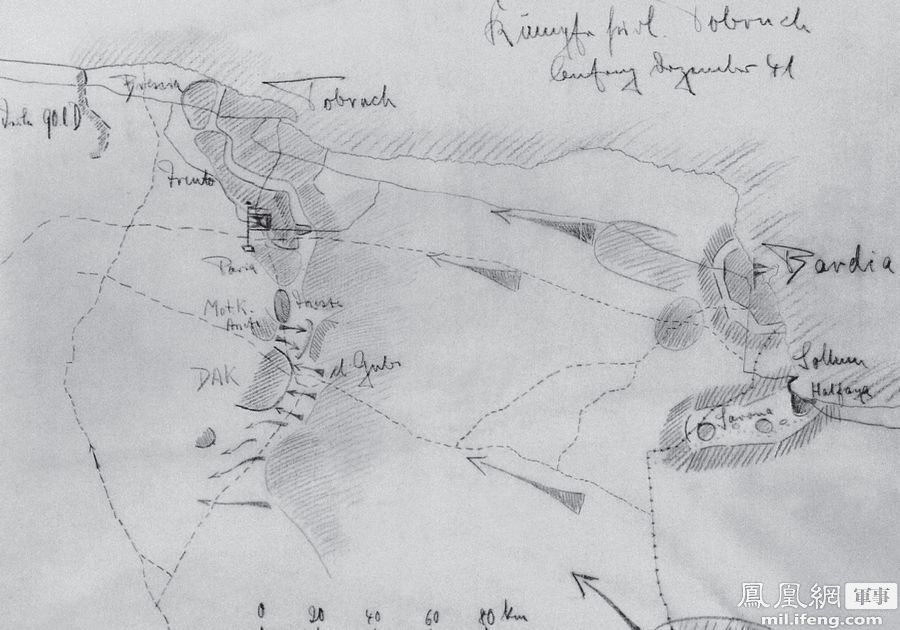时间:4月18日
地点:彼岸书店
嘉宾:
沈艾娣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生平》作者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妍杰该书中文版译者
为什么要给刘大鹏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传?
赵妍杰:今天非常荣幸客串主持。第一个问题我抛给沈老师,在我们强调进步、革命、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中,很难看到刘大鹏这样的普通人,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要为刘大鹏作传?
沈艾娣:其实当时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要作刘大鹏传,是我的老师科大卫教授定下的题目。在写作中,我预期的读者是西方的大学生,我希望让他们认识到,像刘大鹏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只是历史教科书中刻板而遥远的形象。我想告诉他们,在中国近代那样一个激烈的转折时代,刘大鹏这样的僻居乡村、保守而传统的一群人是如何度过的。我觉得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能总是从后向前看,以后人的预设来想象古人,而应当考虑当时的人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世界。
赵妍杰:谢谢沈教授。赵老师,您一直提倡区域社会史研究,您如何评价沈教授的《梦醒子》?
赵世瑜:我和沈艾娣及科大卫教授都很熟悉,实际上沈艾娣教授的做法与科大卫老师最初的设想并不完全契合,但是我知道科大卫私下里对沈艾娣有很高的赞许,正是因为这本书,成功地展示了普通人如何走完那段剧烈变动的时代。我觉得沈艾娣教授始终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当中,与具体情景相联系,使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与乡土的时空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撰写晋祠、赤桥村或是山西的历史。无论切入点在哪里,最终都会由此去透视时代的变化。
他是希望像曾国藩一样,日记之后会被出版
赵妍杰:日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使用日记,挖掘其中的价值呢?
沈艾娣:人写日记是为了创造自己,而不是真实地展示自己,人在写日记时会把自己塑造成应该成为的样子。比如刘大鹏最初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日记会像曾国藩的日记一样被出版。我觉得研究者在利用日记时应该意识到,它虽然是一手史料,但也是一个人为了某种目的而写作的。另外,如果想要通过日记了解一个人,就有必要全面地阅读、理解他的日记。比如已经出版的《退想斋日记》,实际上只是全文的很少一部分,大概是1/10,编者所感兴趣的是他认为跟大的历史有关系的部分,比如重要的事件、风俗习惯这一类的。而刘大鹏的日记中还包括很多道德修养、身体状况的部分都被省略掉了。如果只阅读删节后的版本,我觉得是无法全面理解日记的主人的。
赵世瑜:我觉得利用日记史料,必须注意它出现以及撰写的背景。日记和回忆录等文体在中国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晚至明代中后期。日记无论如何表现的都是对作者有利、作者希望展示出来的内容。我没有体验,因为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近几年大家争得比较厉害的蒋介石日记等等,大概都有类似的特点。日记确实是个人性的,传递的是个人的情感和想法,但它毕竟不同于完全公开的文类。日记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作为很好的社会史研究材料。另外,利用日记必须以其他资料进行佐证。比如刘大鹏与邻村的争议,就不应只以刘本人的日记为依据。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一定要做到的,是我们在判断或者使用日记这类材料的一个原则。
和刘大鹏日记类似的,黄山书社最近出了一套六卷本的江苏常熟人的《许兆玮日记》,时间跨度也是从甲午战争前后,差不多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讲了很多他在家乡常熟做的事。因为他考中的功名比刘大鹏高,所以他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还讲了很多京师的事情,这类日记这些年不断被出版和利用。
国家重要,可是世界对刘大鹏也重要
赵妍杰:赵老师一直提倡区域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反对以国家的框架来填充地方的史料。在沈老师这本书里,虽然是个人的故事,可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国家、社会的革命大主题。在区域研究的方法上怎样才能把国家和地方有机地结合起来,讲出有特色的地方性故事?
沈艾娣:这个很难说,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一定是要解释国家,而是要解释过去,国家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历史研究就像地图,有的标示出不同国家,有的标示到不同的县,有的甚至可以标示到一座房子。这些地图都是有用的。国家是很重要的政治区域,但其他层级的区域也有它的重要意义。同时不同的层级之间存在自然而然的联系,比如赤桥村也受到西伯利亚铁路开通的影响,因为此后茶叶不再经过蒙古和山西,这也影响到山西、赤桥村和刘大鹏。
可是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就要从更高一点看的,从世界史,这些都是重要的,不一定总是要揭示一个国家,当然国家重要,可是世界对刘大鹏也重要。
赵世瑜:我非常赞同沈教授的看法。另外,我需要厘清一个观念,我绝不会反对用国家的框架来研究历史,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下做研究,我觉得他们的研究都很伟大。我以前应该没有这样表述过,今后也不会这样表述,请大家监督。
过去任何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理解生活的意义,都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国家之所以存在且有其意义,就是因为它在人的生活中是有体现的。但问题是,生活层面所体现的国家和国家层面上所体现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立场看国家的。比如国家采取某些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而言,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比如通过物价政策,买菜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国家的存在,因为物价是国家定的。但百姓也有很多办法对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国家的实在性,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度,而是落实在方方面面,应该从生活的实践来理解它。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就学,起源于安徽小岗村,小岗村党支部自己商量商量,决定把土地让老百姓承包了,这个东西本来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大家在底下可能就是那么做的。后来慢慢推广起来,变成了被支持、被倡导的一个方向,这就变成了一种制度、一种政策了,这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像张居正,明代万历年间,他的“一条鞭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老百姓自己搞,地方官也认可,慢慢就在一个小的区域逐渐推广,就上到国家去了。当然也有国家下来的东西,都是双向的。所以我觉得国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它很实在,不仅仅体现在政策或者制度上,也体现在生活实践当中。所以你要在生活实践当中去理解它,要在不同的具体的地方和区域去理解它,才能对这个制度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对国家才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这当然涉及我们研究方法的一种取向。
做历史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赵妍杰:新文化史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它的目的是通过鲜活的个案透视时代的整体风貌。沈教授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似乎也有新文化史影响的印迹,想请问沈教授和赵教授,是怎样看待新文化史、微观史等研究取径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呢?
沈艾娣: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难的问题,因为新文化史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在西方曾经流行,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和西方的史学研究潮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传统思想史在中国很流行,近些年和新文化史也有很好的交汇融合;而在西方,思想史从50年代开始很少有人做,近些年来出现复兴,成为了一种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写的应该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微观史。两个学术界面对不同的国家,面对什么国家当然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兴趣,我们都是面对自己的国家,你们是面对中国。
赵世瑜:刚才沈教授的说法让我们知道不能盲目跟风,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三四十年的时间,慢慢地和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来往多了,所以对他们的很多研究不像以前有那么多隔膜,理解起来也比较快。
所谓新文化史,是接着以前所谓传统的或者旧的文化史,也有人说还有新社会史,和以前的社会史有区别,其实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当前对中西史学界没有那么隔膜,中国对西方的理论、方法,理解很快。新文化史、社会史不能说跟从前的文化史、社会史有太大的区别。以兰克等为代表,史学的面貌曾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进入20世纪,并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转折,而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与人类学之间的影响,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影响。有趣的是,西方新文化史家往往自认为是社会史学家。社会史经历了从经济向文化的转向,新的理论、方法并不是否认,而是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比如科大卫的“礼仪标签”说等,都可以视为这一转向下的产物。但这并不等同于新文化史,后者强调诸如身体、记忆、图像等主题。这类主题对于开拓中国史研究的视野方面有意义,但不宜过度强调。所有研究取向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服务,但也没有必要变成它们。
赵妍杰:提问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您和赵老师对于学术写作的方式有什么看法?学术写作真的一定要艰涩难懂吗?
沈艾娣:历史学是研究,但也是创造一段历史。历史学研究和大众阅读的分离,也是英国和美国的很大问题,我自己也不太想看难理解的书,自己想多看一点故事。但当前西方的历史写作正慢慢回归读者。这种回归不仅仅是微观史等擅长“写故事”的史学体裁,实际上五六十年代也有很多大学者写了不少大题目的书籍,也是人人都能看的,这说明还是存在着把历史“写得好看”的可能。也有一些新方式写作值得参考,比如中国历史学者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采用了很有意思的方法,每章后面都有回忆的文章,既展示了作者的观点,个人的治史经验,也展示了一手的资料,读来很有意思。
赵世瑜: 为什么西方学者的书比中国学者的更好看?我觉得西方很多学者,比如史景迁,更远的爱德华·吉本,他们都是英国人,受到了英国传统的熏陶。英式散文是文学中的重要流派,我觉得也潜移默化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另外,西方很多学者的目标读者是西方大学生,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去改变写作与学术的脱轨。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他们的书不是给领域里的专家写的,而是面向普通的读者。还有中国的学术制度并不支持“讲故事”的写作方式,学者几乎不可能同时得到学术机构和普通读者的认可。
本版录音整理/桑青供图/桑青
观众互动
提问一:从您的写作方面来讲,您一开始拿到刘大鹏日记,是把他当成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从他的日记把这个人物创造出来?还是您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原型,比如说一个举人,然后给他修正?相关的一个问题,历史写作,特别是关系到历史人物的,有创造的过程,还有就是要求真,那么创造和求真之间是什么关系?写作过程中您有没有矛盾或者困惑的地方?
沈艾娣:我开始写刘大鹏时是空白的。如果说创造,写作是创造,不是弄出来一个人。刘大鹏就是一个人,可是我写一本书是一个创造。因为我不可能把刘大鹏的全部日记都写进去,我要选择,要决定哪些部分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创造的工作。但不是创造事实,而是选择哪些事实。就像讲故事,你不可能将全部事情都讲进去,肯定会选择,写书也是这样的,必须要选择。
提问二:我非常惊讶这么好的作品不是由国内学者带给我的,我希望国内的学者也多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读前人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想问的是,假如青年刘大鹏和中年刘大鹏此刻坐在我们中间,如果他想写点东西的话,您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会给他什么建议?您会不会感觉当初刘大鹏要是再写点什么就好了?
沈艾娣:其实刘大鹏的家人也有同样的思想,一个外国人来写爷爷的历史,觉得有一点得意。其实我觉得刘大鹏很可怜,确实是一个好人,可是他能成功的事情不多。他活着时没什么名,就是村里的老人家,人家在街上吵架,他过去,人家就不再吵,因为尊敬他,等他过去以后再吵。很多事情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不是他的错,是世界改变得快,中国这段历史也不是很平安过去的。
提问三:国内学者有大量做刘大鹏的,您作为一个英国学者,跟中国学者面对同一个学术问题时有什么思维上的差异?
沈艾娣:也不一定有差异,当然我们的学术界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刘大鹏是一个人,我们不一样。我开始写就想写这个人的故事,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看,也没想到中国人会感兴趣。因为我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很简单的比如说科举是什么都要解释,所以我们写书可能不一样,就是全部要解释给一个完全陌生的读者。
赵世瑜: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或者学者来看这些不同,非常不一样。其中写过刘大鹏研究的人,可能只有非常少的人真正对那个地方很了解,这样直接会影响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