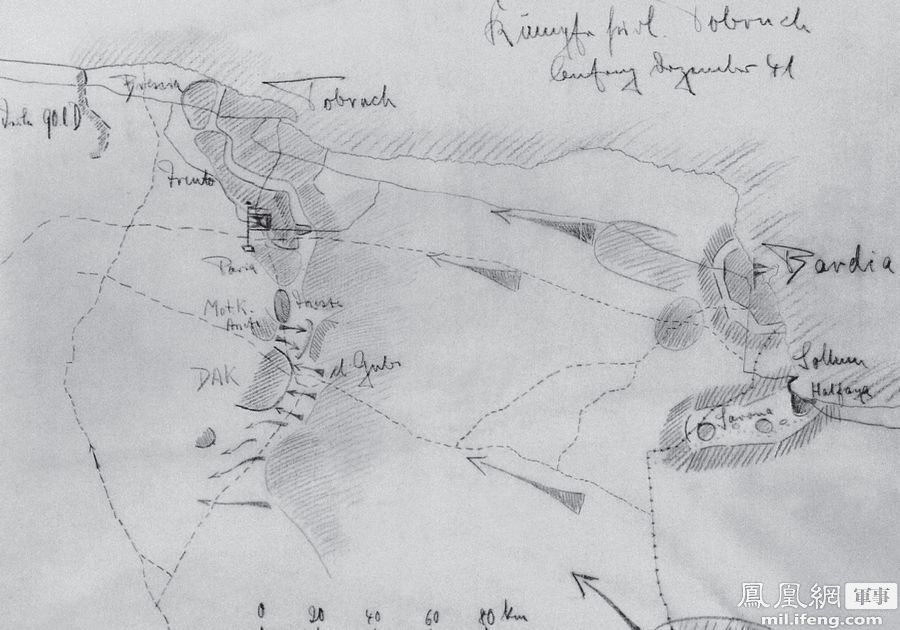由《疯癫与文明》发韧,经过《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演绎,以《知识考古学》的元理论反思为终结,“考古学时期”的福柯倾向于相信,话语有一种内在的自主性生长力量,它似乎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制度和社会实践,隐藏在人所未识的语言学规则之内。在阐发话语明晰性和多样性的努力中,福柯试图重新探讨传统历史观,其基本工具就是所谓的“非连续性”。
福柯认为,连续性历史叙事是通过构造抽象的概念体系来描绘总体化的演化历史的,在此过程中,个体化的话语系列、复杂的相互关系、分散变化的多样性等,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被遮蔽的命运。比如,临床医学的诞生真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吗?福柯反对这种启蒙神话,认为临床医学的诞生不是一个医学技术问题,更与启蒙理性的张扬无关,“而只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亦即能指(医学理论)和所指(医疗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福柯看来,把临床医学的诞生描述为历史的必然逻辑而不是澄清为历史的偶然建构,遮蔽了历史的真相。虽然福柯对临床医学诞生之可能性条件的分析未必是合理的,但他开启了另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结合福柯后来谱系学时期的权力分析,我们看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努力复活了疯癫如何被置于理性对立面的“沉默的考古学”,指出理性与疯癫的对立只不过是为了强化真理的规范而被古典及现代话语建构出来的。这种对立一旦被话语建构出来,疯癫的权利就被彻底剥夺了,疯癫话语在总体历史叙事中从此渺无踪迹了。
考古学时期的福柯还没有发展出谱系学时期的深刻性和颠覆性,他只是试图将断裂、非连续性等概念引入历史分析,从而确定话语的特殊生长规律而已。但前后期福柯怀疑与批判连续性总体历史叙事所造成的压迫和遮蔽是一致并且递进的。福柯的怀疑与批判值得深思。当我们说“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进步运动”时,我们很可能就遮蔽了现代化背后的血与火,遮蔽了落后民族的抗争史和屈辱史,遮蔽了多样性文明及生活方式被驱逐的悲痛事实。
如福柯所说:“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接近它。”福柯区别于连续性总体历史叙事的“不同的方法”就是非连续性的“一般历史叙事”,它展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而是“一个离散的空间”。福柯一生殚精竭虑开显的疯癫、性史、监狱、临床医学等边缘话语,就是被宏大叙事所尘封的一个个“离散空间”。对福柯而言,这种开显既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一个完整的领域被解放了”,话语多样性之可能被彻底地释放了。
尽管福柯将连续性的历史进步论和总体化叙事当作思想敌人,而且一贯对罪犯、疯子等边缘人群抱有同情,但和他的后继者利奥塔、鲍德里亚相比,福柯不失为一位温和的后现代思想者。他从未全盘否定过连续性和总体性,从未像利奥塔那样将所有的一致性都消解于永无休止的指意流之中。福柯拒绝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所谓的“非连续性哲学”,声称他常常故意夸大历史的断裂程度,不过是为了反抗启蒙话语霸权而刻意做出的姿态。福柯对话语“物质性”的强调和他在《知识考古学》之后转入对制度与实践的分析,表明他并非彻底的后现代思想者。